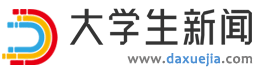大學生新聞網,大學生新聞發布平臺
我們要用怎樣的“尺”去衡量發展? ——《以自由看待發展》讀書報告
一、阿瑪蒂亞·森
這本書的作者,阿瑪蒂亞·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1933年年末,泰戈爾,這位亞洲第一位,也是印度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接受了一個請求:他的秘書希望這位文學巨匠能為自己即將出世的外甥起一個名字。泰戈爾欣然同意,略思片刻后,取名“阿瑪蒂亞(Amartya)”。這個詞的意思是“另一個世界的”,泰戈爾笑著說,“這是一個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這孩子將長成一個杰出的人。”這個孩子,就是在1998年第八個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印度人,阿瑪蒂亞·森。
不知是否是因為作者本身來自發展中國家,他的視角有別于傳統西方學者。一是更切中貧窮等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實質,二是能夠用更平等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平等的首要體現就是他十分關注從婦女到窮人等少數群體的利益,在書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論述性別平等和窮人的福利問題,尤其是貧窮國家的問題。
二、發展是什么?
談到發展,大家會想到什么?在我第一次聽到這本書的名字的時候,我就想,講經濟就講經濟,為什么要扯上倫理呢?一般大家說到發展也就是說GDP或者GNP的增長、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這些東西,把發展扯上自由,開始講倫理,一定非常枯燥無聊。然而讀了之后,發現我的想法是錯誤的。
森在第一章用公元前八世紀一對夫妻的對話來闡釋發展。馬翠依和亞納瓦克亞從怎么變得有錢,討論到“財富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他們得到他們所想要的”。馬翠依說,如果整個世界的財富都屬于她,她也不能實現長生不老,那么我要那些不能讓她長生不老的財富干什么?馬翠依的這個詰問,在印度宗教神學中一遍遍地被引用,用以說明人類困境的本質與物質世界的局限性。亞里士多德也在三千英里意外回應馬翠依的詰問:“財富顯然不是我們追求的東西;因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為其他事物有用。”
所以呢,我們總是向擁有更多的收入或者財富,這并不是因為財富本身令人向往,而是因為,它們總是極好的通用手段,使我們能夠獲得更多自由去享受我們珍視的生活。也就是說,財富的有用性在于它能幫助我們實現不少實質自由。我們現在經常說的實現XX自由,什么車厘子自由啊、蝦滑自由啊,其實都是在通過財富的有用性來滿足這種口欲和精神上的實質自由。但是實現車厘子自由、蝦滑自由其實不一定要靠錢,生活在智利、或者海邊的人生來就擁有這種自由。所以說實質自由并不一定要靠財富來實現,用經濟增長來等于發展也是不對的。
森認為“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 一旦從自由或可行能力視角看待發展,一下子就把發展問題提升到了哲學層面,成為高于其它工具價值的最高價值標準。在這個更高的層面,經濟學就有機會超越對效率的分析,與道德哲學、法哲學和政治哲學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關懷統一起來。
三、為什么要用“自由”這把尺子來衡量發展?
森認為“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這個“真實自由”指的不僅是自由的權利,還包括自由的能力。舉個例子來說,有一個目不識丁的成年人,對數字也一竅不通,他拿著一萬塊大喊“我要炒股票,我要發財!”他當然有炒股的自由,沒有人也沒有法律不允許他炒股。然而他沒有受過教育,不認字也不識數,他怎么炒股?所以他有著“自由的權利”,卻沒有“自由的能力”,而后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森在書里用他親身經歷的一個例子來解釋。森十歲時遇到件令他終身難忘的事:一天,他看到一個穆斯林青年闖入森的家,這個青年被當地的印度教暴徒背后捅了一刀,血流如注。這位穆斯林青年的妻子曾經勸他不要到印度教地區打工,尤其是在雙方矛盾頗深的時節里。但家里太窮,他只能去那里賺點小錢糊口。小阿瑪蒂亞森給他水喝,哭喊著叫家中的大人來幫助,稍后他被小阿瑪蒂亞的父親送去醫院。可惜,這個年輕人傷勢過重,不治身亡。他的名字叫卡德爾·米亞,這個名字森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此悲劇說明:經濟不自由會助長社會不自由,正如社會或政治不自由也會助長經濟的不自由(假如他沒那么窮,就不需要冒著危險去異教徒地區打工)。極度貧困使一個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時成為犧牲品。
要注意,森并沒有從宗教沖突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在這本書里,他從“自由”的角度去分析這個悲劇。這一點是讓我們耳目一新的,如果大家拿著“自由”這把尺來衡量發展的效果,就能得到很多新知。
發展中國家把發展當作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關鍵是,發展意味著什么?朝什么方向發展?那些被看作促進發展的因素,會不會倒過來對發展本身造成損害?所以森用自由這把尺來衡量發展,他認為發展并不是終極目標,自由才是發展的目標,發展只是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而已。
四、貧窮國家的奢侈品?——民主
作者在本書中闡述了婦女問題、人口與糧食問題、人權等一系列問題,在當今時代,本書最引起我深入思考的,還是第六章開始闡述的民主問題。本書中的民主問題,從自由角度理解,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政治自由。從第六章開始,森開始著重探討民主的重要性,他回答了一個問題:對一個窮國來說,經濟需要與民主是否是一個矛盾的選擇。
1、森達班的經濟需要與生命權
作者在開頭舉了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所要闡述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自由的問題。在孟加拉南部與印度西孟加拉相連之處,有一個地方叫森達班,意思為“美麗的森林”。這里的森林中,有相當兇猛的孟加拉虎,也有大量野生蜜蜂生產的蜂蜜。進入森林采集蜂蜜必須防備孟加拉虎的襲擊。好的時候,一年只有50個人因采集蜂蜜死于孟加拉虎的襲擊,但情況糟糕的時候,死者數目就會大得多。貧困驅使森達班的人們為了一兩美元的蜂蜜去冒慘死虎口的風險,這時候要求他們集中注意自由權和政治自由就可能真的顯得很奇怪,人身保護權在這種情況下也可能是無法溝通的概念。所以,就有人主張,當然必須優先考慮滿足經濟需要,他們認為民主和政治自由是貧困國家所不能承擔的奢侈品。
這種分析思路確立已久,并為中國、新加坡等東亞發展中國家竭力倡導。但按照這種分析思路,又可以問出一個問題:什么應該是第一位的?是消除貧困和痛苦,還是保障那些其實對于窮人來說看起來并沒有多少用處的政治自由權和公民權利?
2、李光耀命題
作者提出了李光耀命題來解釋這一問題。在李光耀擔任總理的31年內,新加坡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人均GDP增加超過34倍,在1991年達到14504美元。李光耀實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轉口貿易,促進經濟自由,重視法治,與此同時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抑制貧富差距,創造了繁榮的景象。而在硬幣的另一面,在新加坡個人的言論自由、政治權利的缺失是一直被評論家詬病的。這就被森稱之為“李光耀命題”。作者是鮮明地反對李光耀命題的,也就是威權主義政府并不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也許大家會說,可是在這些威權主義政府下,經濟確確實實得到發展了呀!我們看見了森林,還要看見其中的樹木。進一步考察并檢視經濟增長所設計的因果性過程,我們會發現,導致東亞經濟體成功的政策清單包括:開放競爭、運用國際市場、高識字率和高就學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對投資、出口和工業化積極性的公共支持。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上述任何政策與更多的民主是不相容的,或者這些政策必須要靠那些威權主義因素來維持。
森認為經濟發展與政治自由不是對立的關系,也不存在先后的順序關系。對于一個窮國來說,民主同樣重要而緊迫,不能為了得到一方而放棄另一方,他鮮明地反對李光耀命題,對于窮人在政治自由和經濟需要之間選擇后者的爭辯,他認為民主的實踐與民主的正當性之間不是矛盾的,即便在當下,窮人認為經濟需要是更迫切的,那也并不妨礙他們享有政治權利。當然也許有人會說,窮人沒受過教育,根本沒有能力參與民主啊。那窮人有沒有能力參與是一回事,有沒有權利參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前者無法成為后者的理由。正如森指出的,只有當我們需要民主時,才會想起它的保障性作用。現實中我們卻往往由于短視而對民主的作用視而不見,一旦喪失民主,自身就會陷入種種風險。比如亞洲金融危機,危害主要由社會底層承擔。民主體制并非機械性的發展工具,它的作用取決于如何使用,良好運作才能發揮實效。
3、饑荒
他認為饑荒的防止有兩個因素:激勵因素和信息。“在這個世界的不同國家中,饑荒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但卻不曾殺死統治者。國王和總統、官僚和各級主管、軍方的領導人和指揮官,他們從來不是饑荒的受害者。如果沒有選舉,沒有反對黨,沒有不受審查的公共批評的活動空間,掌權者就不會因為防止饑荒失敗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另一方面,民主卻會把饑荒的懲罰作用傳遞給統治集團和政治領導人,這就給了他們以政治的激勵因素去防止任何有威脅性的饑荒。”其二是信息,新聞媒體受民主制度的激勵去披露事實而置政府于窘境,這使得領導人能夠盡早接收到饑荒的信息預警。
森說出版自由和活躍的政治反對派是受饑荒威脅的國家所能擁有的最好的早期警示系統。通過信息公開,反對派的施壓,促使政府采取公共措施增加人們的購買力。在大躍進時期,信息被阻隔,沒有自由的言論和媒體,政府收到的只是虛假的粉飾太平的報告。從前有和一個經歷過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的長輩聊過,他說饑荒發生的時候,本來有三種途徑可以使人活命,首先是老百姓自發的逃荒,第二種是民間自然的救助機制,哪怕是奸商,也可以把糧食運到有需要的地方。第三種是政府賑災,而在那時的中國不許老百姓逃荒,可是特權階層卻大量浪費糧食,而民間的平行救濟又被計劃經濟所阻礙。在縱向的決策方面,由于信息阻礙,決策不透明,政府和民間缺乏自由的溝通機制,而民主的治國方式,包括多黨選舉和公開的媒體,使民主的防護性保障功能得以發揮,印度自1947年實行民主制度后,就沒有發生過饑荒,證明了這一點。
4、民主的顯著意義
森論述了民主的顯著意義在于三個不同的方面:(1)自身固有的重要性;(2)工具性貢獻;(3)在價值標準和規范形成中的建設性作用。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可以理解為我們有自由去選擇我們實際上可能選擇、也可能不選擇的某一事物;工具性貢獻指的是人們運用民主來爭取切身的權利與權益(例證:饑荒不幾乎不發生在民主國家);建設性作用指的是通過自由的公開討論來建設起社會的共識,不僅對于討論的問題本身有好處,對于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和運作也是重要的。(例證:印度克拉拉邦的生育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森并不是一昧地在闡述民主的優越性,因為他認為這又夸大其實效性的危險。對于防止那些容易被理解并且特別能引起直接同情的災難,民主或許是極其成功的。饑荒就是這種災難的典型,但對于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也不能很好地解決。比如,印度在實行民主制度之后根除了饑荒,但在消除日常的營養不良、減少長期存在的文盲和兩性不平等這些方面卻做的不好。這是因為饑荒這種災難很容易被訴諸政治化,因為它很能引起全國人民的共情、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而其他的兩性不平等這些問題則需要公眾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與政治參與才能實現,也就是要更充分運用民主。
五、一些超越所談內容的感想
森還注意到了在價值觀輸出方面東西方的不平等,或者更深一步說,是文化之間價值觀的差異。在全球化趨勢不可阻遏的今天,作為價值觀輸出弱勢一方,不應該妄自菲薄,固守傳統不放,要知道文化本身就在一刻不停地流動,留守所謂的純粹性是違反其本質的。對于價值觀強勢一方,作者提醒他們寬容才是促進發展的美德。
值得敬佩的是,作者對東方文化令人驚嘆的了解程度,他不僅對古印度典籍和佛經中的故事信手拈來,對孔子,伊斯蘭,亞當斯密理論穿插引用,直接地讓我們看見對不同文化強大包容心造就更寬廣的胸懷和視野。對于我自己的啟示則是,我應該更好的了解我從哪里來。我們通常在自己狹窄的軌跡中生活,我們看待事物的觀點總是受主流價值觀的牽引,我們懼怕“自由”,我們總是強調自信,但盲目的自信往往是受利用。我應該要多有一些社會學的想象力,多思考我為什么成為我,我們為什么成為我們,有更深刻的本土意識,才不至于在話語權主導下大潮里頭昏腦漲。
這本書的作者,阿瑪蒂亞·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1933年年末,泰戈爾,這位亞洲第一位,也是印度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接受了一個請求:他的秘書希望這位文學巨匠能為自己即將出世的外甥起一個名字。泰戈爾欣然同意,略思片刻后,取名“阿瑪蒂亞(Amartya)”。這個詞的意思是“另一個世界的”,泰戈爾笑著說,“這是一個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這孩子將長成一個杰出的人。”這個孩子,就是在1998年第八個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印度人,阿瑪蒂亞·森。
不知是否是因為作者本身來自發展中國家,他的視角有別于傳統西方學者。一是更切中貧窮等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實質,二是能夠用更平等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平等的首要體現就是他十分關注從婦女到窮人等少數群體的利益,在書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論述性別平等和窮人的福利問題,尤其是貧窮國家的問題。
二、發展是什么?
談到發展,大家會想到什么?在我第一次聽到這本書的名字的時候,我就想,講經濟就講經濟,為什么要扯上倫理呢?一般大家說到發展也就是說GDP或者GNP的增長、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這些東西,把發展扯上自由,開始講倫理,一定非常枯燥無聊。然而讀了之后,發現我的想法是錯誤的。
森在第一章用公元前八世紀一對夫妻的對話來闡釋發展。馬翠依和亞納瓦克亞從怎么變得有錢,討論到“財富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他們得到他們所想要的”。馬翠依說,如果整個世界的財富都屬于她,她也不能實現長生不老,那么我要那些不能讓她長生不老的財富干什么?馬翠依的這個詰問,在印度宗教神學中一遍遍地被引用,用以說明人類困境的本質與物質世界的局限性。亞里士多德也在三千英里意外回應馬翠依的詰問:“財富顯然不是我們追求的東西;因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為其他事物有用。”
所以呢,我們總是向擁有更多的收入或者財富,這并不是因為財富本身令人向往,而是因為,它們總是極好的通用手段,使我們能夠獲得更多自由去享受我們珍視的生活。也就是說,財富的有用性在于它能幫助我們實現不少實質自由。我們現在經常說的實現XX自由,什么車厘子自由啊、蝦滑自由啊,其實都是在通過財富的有用性來滿足這種口欲和精神上的實質自由。但是實現車厘子自由、蝦滑自由其實不一定要靠錢,生活在智利、或者海邊的人生來就擁有這種自由。所以說實質自由并不一定要靠財富來實現,用經濟增長來等于發展也是不對的。
森認為“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 一旦從自由或可行能力視角看待發展,一下子就把發展問題提升到了哲學層面,成為高于其它工具價值的最高價值標準。在這個更高的層面,經濟學就有機會超越對效率的分析,與道德哲學、法哲學和政治哲學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關懷統一起來。
三、為什么要用“自由”這把尺子來衡量發展?
森認為“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這個“真實自由”指的不僅是自由的權利,還包括自由的能力。舉個例子來說,有一個目不識丁的成年人,對數字也一竅不通,他拿著一萬塊大喊“我要炒股票,我要發財!”他當然有炒股的自由,沒有人也沒有法律不允許他炒股。然而他沒有受過教育,不認字也不識數,他怎么炒股?所以他有著“自由的權利”,卻沒有“自由的能力”,而后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森在書里用他親身經歷的一個例子來解釋。森十歲時遇到件令他終身難忘的事:一天,他看到一個穆斯林青年闖入森的家,這個青年被當地的印度教暴徒背后捅了一刀,血流如注。這位穆斯林青年的妻子曾經勸他不要到印度教地區打工,尤其是在雙方矛盾頗深的時節里。但家里太窮,他只能去那里賺點小錢糊口。小阿瑪蒂亞森給他水喝,哭喊著叫家中的大人來幫助,稍后他被小阿瑪蒂亞的父親送去醫院。可惜,這個年輕人傷勢過重,不治身亡。他的名字叫卡德爾·米亞,這個名字森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此悲劇說明:經濟不自由會助長社會不自由,正如社會或政治不自由也會助長經濟的不自由(假如他沒那么窮,就不需要冒著危險去異教徒地區打工)。極度貧困使一個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時成為犧牲品。
要注意,森并沒有從宗教沖突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在這本書里,他從“自由”的角度去分析這個悲劇。這一點是讓我們耳目一新的,如果大家拿著“自由”這把尺來衡量發展的效果,就能得到很多新知。
發展中國家把發展當作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關鍵是,發展意味著什么?朝什么方向發展?那些被看作促進發展的因素,會不會倒過來對發展本身造成損害?所以森用自由這把尺來衡量發展,他認為發展并不是終極目標,自由才是發展的目標,發展只是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而已。
四、貧窮國家的奢侈品?——民主
作者在本書中闡述了婦女問題、人口與糧食問題、人權等一系列問題,在當今時代,本書最引起我深入思考的,還是第六章開始闡述的民主問題。本書中的民主問題,從自由角度理解,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政治自由。從第六章開始,森開始著重探討民主的重要性,他回答了一個問題:對一個窮國來說,經濟需要與民主是否是一個矛盾的選擇。
1、森達班的經濟需要與生命權
作者在開頭舉了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所要闡述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自由的問題。在孟加拉南部與印度西孟加拉相連之處,有一個地方叫森達班,意思為“美麗的森林”。這里的森林中,有相當兇猛的孟加拉虎,也有大量野生蜜蜂生產的蜂蜜。進入森林采集蜂蜜必須防備孟加拉虎的襲擊。好的時候,一年只有50個人因采集蜂蜜死于孟加拉虎的襲擊,但情況糟糕的時候,死者數目就會大得多。貧困驅使森達班的人們為了一兩美元的蜂蜜去冒慘死虎口的風險,這時候要求他們集中注意自由權和政治自由就可能真的顯得很奇怪,人身保護權在這種情況下也可能是無法溝通的概念。所以,就有人主張,當然必須優先考慮滿足經濟需要,他們認為民主和政治自由是貧困國家所不能承擔的奢侈品。
這種分析思路確立已久,并為中國、新加坡等東亞發展中國家竭力倡導。但按照這種分析思路,又可以問出一個問題:什么應該是第一位的?是消除貧困和痛苦,還是保障那些其實對于窮人來說看起來并沒有多少用處的政治自由權和公民權利?
2、李光耀命題
作者提出了李光耀命題來解釋這一問題。在李光耀擔任總理的31年內,新加坡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人均GDP增加超過34倍,在1991年達到14504美元。李光耀實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轉口貿易,促進經濟自由,重視法治,與此同時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抑制貧富差距,創造了繁榮的景象。而在硬幣的另一面,在新加坡個人的言論自由、政治權利的缺失是一直被評論家詬病的。這就被森稱之為“李光耀命題”。作者是鮮明地反對李光耀命題的,也就是威權主義政府并不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也許大家會說,可是在這些威權主義政府下,經濟確確實實得到發展了呀!我們看見了森林,還要看見其中的樹木。進一步考察并檢視經濟增長所設計的因果性過程,我們會發現,導致東亞經濟體成功的政策清單包括:開放競爭、運用國際市場、高識字率和高就學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對投資、出口和工業化積極性的公共支持。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上述任何政策與更多的民主是不相容的,或者這些政策必須要靠那些威權主義因素來維持。
森認為經濟發展與政治自由不是對立的關系,也不存在先后的順序關系。對于一個窮國來說,民主同樣重要而緊迫,不能為了得到一方而放棄另一方,他鮮明地反對李光耀命題,對于窮人在政治自由和經濟需要之間選擇后者的爭辯,他認為民主的實踐與民主的正當性之間不是矛盾的,即便在當下,窮人認為經濟需要是更迫切的,那也并不妨礙他們享有政治權利。當然也許有人會說,窮人沒受過教育,根本沒有能力參與民主啊。那窮人有沒有能力參與是一回事,有沒有權利參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前者無法成為后者的理由。正如森指出的,只有當我們需要民主時,才會想起它的保障性作用。現實中我們卻往往由于短視而對民主的作用視而不見,一旦喪失民主,自身就會陷入種種風險。比如亞洲金融危機,危害主要由社會底層承擔。民主體制并非機械性的發展工具,它的作用取決于如何使用,良好運作才能發揮實效。
3、饑荒
他認為饑荒的防止有兩個因素:激勵因素和信息。“在這個世界的不同國家中,饑荒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但卻不曾殺死統治者。國王和總統、官僚和各級主管、軍方的領導人和指揮官,他們從來不是饑荒的受害者。如果沒有選舉,沒有反對黨,沒有不受審查的公共批評的活動空間,掌權者就不會因為防止饑荒失敗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另一方面,民主卻會把饑荒的懲罰作用傳遞給統治集團和政治領導人,這就給了他們以政治的激勵因素去防止任何有威脅性的饑荒。”其二是信息,新聞媒體受民主制度的激勵去披露事實而置政府于窘境,這使得領導人能夠盡早接收到饑荒的信息預警。
森說出版自由和活躍的政治反對派是受饑荒威脅的國家所能擁有的最好的早期警示系統。通過信息公開,反對派的施壓,促使政府采取公共措施增加人們的購買力。在大躍進時期,信息被阻隔,沒有自由的言論和媒體,政府收到的只是虛假的粉飾太平的報告。從前有和一個經歷過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的長輩聊過,他說饑荒發生的時候,本來有三種途徑可以使人活命,首先是老百姓自發的逃荒,第二種是民間自然的救助機制,哪怕是奸商,也可以把糧食運到有需要的地方。第三種是政府賑災,而在那時的中國不許老百姓逃荒,可是特權階層卻大量浪費糧食,而民間的平行救濟又被計劃經濟所阻礙。在縱向的決策方面,由于信息阻礙,決策不透明,政府和民間缺乏自由的溝通機制,而民主的治國方式,包括多黨選舉和公開的媒體,使民主的防護性保障功能得以發揮,印度自1947年實行民主制度后,就沒有發生過饑荒,證明了這一點。
4、民主的顯著意義
森論述了民主的顯著意義在于三個不同的方面:(1)自身固有的重要性;(2)工具性貢獻;(3)在價值標準和規范形成中的建設性作用。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可以理解為我們有自由去選擇我們實際上可能選擇、也可能不選擇的某一事物;工具性貢獻指的是人們運用民主來爭取切身的權利與權益(例證:饑荒不幾乎不發生在民主國家);建設性作用指的是通過自由的公開討論來建設起社會的共識,不僅對于討論的問題本身有好處,對于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和運作也是重要的。(例證:印度克拉拉邦的生育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森并不是一昧地在闡述民主的優越性,因為他認為這又夸大其實效性的危險。對于防止那些容易被理解并且特別能引起直接同情的災難,民主或許是極其成功的。饑荒就是這種災難的典型,但對于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也不能很好地解決。比如,印度在實行民主制度之后根除了饑荒,但在消除日常的營養不良、減少長期存在的文盲和兩性不平等這些方面卻做的不好。這是因為饑荒這種災難很容易被訴諸政治化,因為它很能引起全國人民的共情、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而其他的兩性不平等這些問題則需要公眾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與政治參與才能實現,也就是要更充分運用民主。
五、一些超越所談內容的感想
森還注意到了在價值觀輸出方面東西方的不平等,或者更深一步說,是文化之間價值觀的差異。在全球化趨勢不可阻遏的今天,作為價值觀輸出弱勢一方,不應該妄自菲薄,固守傳統不放,要知道文化本身就在一刻不停地流動,留守所謂的純粹性是違反其本質的。對于價值觀強勢一方,作者提醒他們寬容才是促進發展的美德。
值得敬佩的是,作者對東方文化令人驚嘆的了解程度,他不僅對古印度典籍和佛經中的故事信手拈來,對孔子,伊斯蘭,亞當斯密理論穿插引用,直接地讓我們看見對不同文化強大包容心造就更寬廣的胸懷和視野。對于我自己的啟示則是,我應該更好的了解我從哪里來。我們通常在自己狹窄的軌跡中生活,我們看待事物的觀點總是受主流價值觀的牽引,我們懼怕“自由”,我們總是強調自信,但盲目的自信往往是受利用。我應該要多有一些社會學的想象力,多思考我為什么成為我,我們為什么成為我們,有更深刻的本土意識,才不至于在話語權主導下大潮里頭昏腦漲。
- 作者:張星樂 來源:大學生新聞網
- 發布時間:2023-08-24 瀏覽:
- 我們要用怎樣的“尺”去衡量發展? ——《以自由看待發展》讀書報
- 08-24 關注:0
- 霧必隱花乎
- 08-19 關注:8
- 送你一束紫色風信子
- 08-19 關注:9
- 稻谷色的秋季
- 08-19 關注:8
- 如何獲得幸福
- 08-10 關注:9
- 大學生畢業作品展風采
- 5月18日,觀眾在博覽會上參觀手造作品。當日,山東工藝美術學院2023年設計藝術博覽會在濟南舜耕國際會展中心開展。
- 05-19 關注:13
- 千年渡口
- 均溪浩蕩向東流,閩地高才古渡頭。
- 04-04 關注:19
- 人生百年經驗談
- 人生百年經驗談,銘記在心五句話。
- 04-04 關注:25
-
客服QQ:471708534 大學生新聞網©版權所有